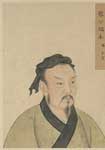
端木賜(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復姓端木,字子貢。儒商鼻祖,春秋末年衛國黎(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人。孔子的得意門生,儒客杰出代表,孔門十哲之一,善于雄辯,且有干濟才,辦事通達,曾任魯國、衛國的丞相。還善于經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端木遺風”指子貢遺留下來的誠信經商的風氣,成為民間信奉的財神。子貢善貨殖,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風,為后世商界所推崇。
《論語》中對其言行記錄較多,《史記》對其評價頗高。子貢死后,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儒商始祖
子貢不僅在學業、政績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財經商上也有著成就。《論語·先進》載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則屢中”,意思是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卻窮得丁當響,連吃飯都成問題,而子貢不被命運擺布,猜測行情,且每每猜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翻譯:子貢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做買賣,以成巨富。由于子貢在經商上大獲成功,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相當的筆墨對這位商業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經濟發展上所起的作用。
魯衛之相
《論語》僅說子貢在“言語”方面優異,這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人們對子貢在其它方面的才能的認識。《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子貢“常相魯、衛”。他的老師孔子也認為子貢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論語·雍也》曾記載季康子問孔子子路、子貢、冉求是否可以從政,孔子回答說三人皆可從政,但孔于卻分別道出三人之優點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賜(子貢)也達”、“求(冉求)也藝”。從孔子列舉的三個優點看,我們覺得子貢的優點——“達”,似乎更是從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謂“達”就是通達事理,試想一個從政的人如果能夠“通達事理”,他就會高屋建瓴,從宏觀上把握問題的全局和整體,把政事處理得有條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斷)、冉求的“藝”(多才多藝),都不過是從政必需之一端。正因為子貢通達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語”才能,所以他才會被魯、衛等國聘為相輔。正因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會在出使齊、吳、越、晉四國的外交活動中得心應手,獲得圓滿成功。
教書育人
子貢的晚年,也像孔子一樣開始教學,魯國大夫子服景伯就是他培養出的人才。
子貢尊師
相傳,孔子有七十二個有名的弟子,子貢便是其中之一。萬仞宮墻典故,出自子貢稱贊孔夫子之學問高深。子貢尊師的故事,也很感人。一次,魯國大夫在別人面前貶低孔子,抬高子貢。子貢聽說后非常氣憤,他當即以房子打比方,說老師的圍墻高幾丈,屋內富麗堂皇,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到的;而自己不過是只有肩高的圍墻,一眼就可望盡。他還把老師比做太陽和月亮,說老師光彩照人,不是常人所能超越的。孔子死后,子貢悲痛萬分,在孔子墓旁住下,守墓6年。
子貢問道
人的才能和德行,自古以來就少有能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有長處,也必定會有短處。倘若用其長處去彌補短處,那么,天下將沒有人不被使用;倘若苛責人的短處而舍棄其長處,那么,天下人都將被棄而不用。再加上人的感情各有愛憎,旨趣各有同異,即使是像伊尹、周公這樣圣明的人和象墨翟、楊朱這樣的賢能者,如果去征求眾 人對他們的意見的話,誰能免去受譏刺和遭疑忌呢?
子貢向孔子問道:“鄉里的人都喜歡這個人,這個人怎么樣?”孔子說:“不行啊。”子貢又問:“鄉里的人都憎惡他,這個人又怎樣呢?”孔子說道:“也不行啊。最好是鄉里的好人都喜歡他,而鄉里的壞人都憎惡他。”這是因為君子和小人的意趣一定相反,小人憎惡君子也就像君子憎惡小人一樣。要想探明真實的情況,取決于慎重地聽取反映。聽取君子的話,就廢止了小人的邪道;而聽取小人的話,君子的正道就會消亡。
子貢贖人
一切大多數人都做不到的道德,都是偽道德。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氣那么重要。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翻譯:魯國有一條法律,魯國人在國外淪為奴隸,有人能把他們贖出來的,可以到國庫中報銷贖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貢(端木賜)在國外贖了一個魯國人,回國后拒絕收下國家賠償金。孔子說:“賜呀,你采取的不是好辦法。從今以后,魯國人就不肯再替淪為奴隸的本國同胞贖身了。你如果收回國家的補償金,并不會損害你的行為的價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錢,別人就不肯再贖人了。”
“子貢贖人”自損財物做了一件好事,本應該被樹為道德典范,孔子為何反而要批評他?其實魯國那條法律的用意是為了鼓勵每一個人只要有機會,就可以惠而不費地做一件大好事,那怕你暫時沒有預付贖金的能力,也應該去借來贖金為同胞贖身,因為你不會損失任何東西。子貢的錯誤在于把原本人人都能達到的道德標準超拔到了大多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如果魯國君主為子貢之舉樹為典范,大肆通報、嘉獎、宣傳乃至全國推廣,會有什么后果?一、社會表面的道德標準提高了,人人都表態向子貢學習;二、道德水準的實際狀況其實滑坡了,因為頭頂已經高懸了子貢這樣的道德高標,誰若贖回同胞后再去領取國家的贖金就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然而又有幾個人有足夠的財力可以保證損失這筆贖金不至于影響自己的生活呢?
違反常情、悖逆人情的道德是世上最邪惡的東西。《道德經》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崇尚自然的本真質樸,不標榜不偏執,這是中華上古的傳統美德和智慧。因為無數的教訓已經告訴我們:把道德的標準無限拔高,或者把個人的私德當作公德,兩種做法只會得到一個結果,這就是讓道德尷尬,讓普通民眾聞道德而色變進而遠道德而去!
子貢與孔子孰賢
道德第一:孔子說,顏回賢于子貢,這是在道德與學習層次上講的,當然道德上孔子自是高于顏回的。時評第二:時時有人言,子貢賢于孔子。貢獻第三:鎖定春秋,子貢的貢獻是巨大的,通達事理,兩國宰相,能言善辯,縱橫五國,自述第四:用子貢自己的說法是:譬諸宮墻,賜(子貢)之墻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他的話“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高度評價了孔子,維護了老師的名聲,但是只說了孔子的墻高比自己高,并沒有說,自己與孔子的宗廟孰美。高山流水第五:孔子如高山,子貢如流水,高山巍峨,融冰化水方有流水涔涔;流水靈動,源遠流長滋養萬物之德,由是觀之,高山與流水孰賢?
學習能力
子貢學習上的優異,他的“言語”水平高超。《論語·先進》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予、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可見子貢是“言語”方面的優異者,也就是說子貢在說話技巧、演講技能上有獨到之處。據《左傳》等史書可知,在孔子那個時代,外交禮賓人員的語言訓練主要取之于《詩》,這已成為當時的一種習尚。孔子也曾說:“不學《詩》,無以言”,《詩》已成為當時語言訓練的主要教本。《詩》就是后來成為“六經”之一的《詩經》。
在《詩》的學習中,孔子不僅要求學子們搞通弄懂《詩》的本來意義,而且要求他們能對《詩》“活學活用”,在外交禮賓場合能順手拈來以達己意,而這,沒有相當的靈活性和敏銳性是難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門徒中,子貢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論語·學而》曾記載孔子、子貢師徒二人對答,子貢靈活運用《詩經·衛風·淇奧》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詩句來回答老師提問的情形。孔子認為子貢的回答十分貼切,“斷章取義”恰到好處,故而稱贊子貢:“始可與言《詩》已矣”,而且說子貢“告諸往而知來者”,認為他對該詩的理解達到了心領神會的地步。
在《論語》中給予弟子“始可與言《詩》已矣”這樣高度評價的還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學”上的優異者,這說明子貢不僅在“言語”上極為優異,即使在“文學”方面也毫不遜色于 子游、子夏之徒。’《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說:“子貢利口巧辯,孔子常黜其辯”,看來師徒二人經常爭辯一些問題。使子貢在“言語”方面才能大加發揮的當屬他赴齊、吳、越、晉四國的穿梭外交活動了。在這次外交活動中,子貢充分發揮自己的演說才能,使得四國國君對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紛紛采納他的主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具體而言就是: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高超的演說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動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時人評論
子貢在學問、政績、理財經商等方面的表現有目共睹,有耳共聞,故其名聲地位雀躍直上,甚至超過了他的老師孔子。當時魯國的大夫孫武就公開在朝廷說:“子貢賢于仲尼”。魯國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孫武叔的話轉告了子貢,但子貢謙遜地說:“譬諸宮墻,賜(子貢)之墻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說:自己的那點學問本領好比矮墻里面的房屋,誰都能看得見,但孔子的學問本領則好比數仞高墻里面的宗廟景觀,不得其門而入不得見,何況能尋得其門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諸位才有這樣不正確的看法。當時魯國的另一個大臣陳子禽聽到子貢的這通解釋不以為然,他說:“子為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⒇”意謂你不過是謙恭罷了,難道仲尼真的比你強嗎? 總之,所有這些對子貢的贊譽并非空穴來風,它說明子貢在當時的名聲、地位和影響,確實已不在他的老師孔子之下。司馬遷作為有遠見卓識的史學家,他在《史記》中甚至認為孔子的名聲之所以能布滿天下,儒學之所以能成為當時的顯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子貢推動的緣故。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寫道:“七十子之徒賜(子貢)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執而益彰乎?”孔子得“執”子貢而“益彰”實是不刊之論。試想子貢當年“常相魯、衛”,出使列國,各國待之以上賓,其地位顯赫一時,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俐齒;每到一處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帶宣講其老師的一套理論和主張,盡管孔子的那些理論主張有的與時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貢的面上,總要聽一聽,這在客觀上就推銷了孔子。孔子的儒學成為顯學,孔子的名聲布滿天下,實與得“執”子貢這位高足弟子有關。司馬遷對此看得很準。
子貢與顏回
盡管子貢有著多方面的建樹與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卻表現得非常謙。《論語·公冶長》記孔子問子貢:“汝與回也孰愈(誰更強些)?”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門生,子貢對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貢提這樣的問題。子貢相當有涵養,他說:“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實到底子貢與顏回哪個強,世人有目共睹。子貢與顏回比,就政事言,顏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顏回連生計也幾乎維持不下去,《論語》說他“屢空”,看來斷炊的事情亦經常發生,而子貢卻是“家累千金”;論彰揚其師之美名,顏回更沒有子貢那樣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難、遭險惡時,子貢總能挺身而出,顯其大智大勇。《史記·孔子世家》曾載孔子困陳、蔡,絕糧,情形十分危急,而當時孔子門徒個個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是“子貢使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貢是孔門弟子中之最杰出者其中之一。